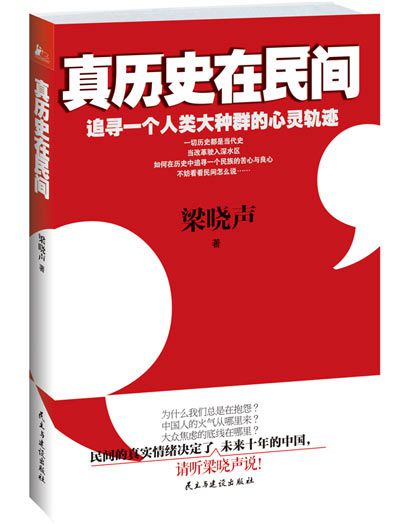
作家梁晓声新作《真历史在民间》近日推出,和往昔出版的时评著作一样,梁晓声依然以执着的态度,直面转型社会时期中国社会的痼疾,字里行间灌注着作家深沉的“忧史”之心。
这是梁晓声近年来最耗费心血的一部作品,一个个时代,一个个社会群体,一个个社会现象……都成为他剖解“微型中国”揭示历史病相的鲜活样本,以事态、事实、以鲜活的不同阶层状况采样脉诊国情,这也是他一直秉承的风格。来自“民间视角”讲述的国家历史,保持了以往的梁式叙事文风,以故事的方式告诉读者,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以及当今中国的现实。
梁晓声奉行“文学要使社会进步,使人的心性提升”的主张,他曾笑谈:“人类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与普通动物相比,如果心性不得到提升,人类甚至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好、最凶恶的动物。”而文学的终极意义,梁晓声认为,正是使我们的心性变得更豁达、更开朗,更善于自我化解忧愁、化解烦闷。
新作完成后,梁晓声就作品回答了该书编辑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新作《真历史在民间》剖析了1950年代到1990年代现实社会的变化,与你之前一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有什么关系?
梁晓声: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公民”者,国家共有者也。
如今,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很差。这乃是由相当畸形的“中国特色”所决定了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级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级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摆这一点。
中国的农民们先天其实都是并不狡猾的。如果说他们现在有点儿狡猾了,那也是后天学的。贫富悬殊是造成年代动荡不安的飓风。经济现象是形成那飓风的气候。时代的转折点始于中国农村,今天受到猛烈冲击和震荡的却是中国城市……
问:《真历史在民间》开篇对“中国女性扫描”,近年女性较之历史上的女性,有何不同?
梁晓声:“当代女性”四个字,越来越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每每显得暖昧的概括。除了性别,她们之中的任何一类,几乎无法在其他诸方面“代表”同性的姐妹们。今天,似乎女性自己们挖空心思地“艺术化”女性的身体。一个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实在并不困难。男人可以舍得花钱“包装”他所爱的女人,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
在从前的中国,丫环中不乏幽默者,而小姐们必须人前特别庄重的。小姐们不敢太幽默,怕失了“大家闺秀”的风范。正如丫环们不敢庄重,只有低三下四地循规蹈矩,怕被人讥为装小姐样儿。当代姑娘装模作样的玩世不恭,和封建社会思春不禁的公主小姐们装模作样的假正经,一码事。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出息,不是因为女人在数量上太多,而是因为男人在质量上太劣。总有一天时代将宣布,它不需要太多的“书生”,他们过剩了。而女人们也将宣布,她们看重的不止是男人的文凭和学历。
问:你在新书中评论了日本与德国的不同,提出要警惕这个“邻国”,这是否为民间交流造成障碍?
梁晓声:须知,一个民族很容易变得心理低贱。日本人曾被视为“冷血动物”。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变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备感周身发寒。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一只豹子面对几头肥鹿和一只松鼠,它当然要先对肥鹿们张牙舞爪扑过去了。这在动物界,叫做猎食本能。而在人类,对于法西斯主义,叫做侵略本能。区别是,仅仅是——一个那样干了; 一个时时暗示全世界:只要我想干。
一人对一人的报复,血溅数尺,以取命为快。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报复,常见于黑社会间的砍杀。一族人对一族人的报复,则每每导致灭族之灾。一国人对一国人的报复,乃人类历史上最恐怖之事。中国并非一个动不动就容易被煽起偏激的民族情绪的国家。在中国,所谓民族情绪,其实往往是被欺辱到了极点才产生的情绪。
一个成熟的国家和民族,首先应是一个相信自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国家和民族。平和就能使人宽厚。宽厚就能使一个民族懂得在国际关系中分寸的必要性。一个国家在它的内部相对公平地解决了或解决着贫富问题,它才会在国际上显示出它的自强姿态。作为国家,是一定要尽最大的能力关怀和体恤到它的普遍子民的。一个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脸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问:《真历史在民间》,民间记录历史,较官方有何不同?
梁晓声:我所谓的“民间”,是将伟人、达官、名流、富商巨富们划入另册,所剩的那一部分人间。在古代,曰“苍生”的那一部分人间。一个社会好不好,或有没有希望,有多大希望,不仅看官员们是些怎样的官员,富人们是些怎样的富人,各类精英是些怎样的精英;也还要看民间是怎样的民间。
现在的我,是很“看好”民间的。今日之民间,总算开始觉醒了一件事——民间原本是比别的社会层面更多温暖的一大部分人间,是最能自然地体现人性的一大部分人间;种种不堪回首之事大规模地发生于民间,实在是因为被肮脏严重地污染了。民间之良心开始复苏,种种被遮蔽,掩盖、歪曲、随心所欲涂改之历史真相,也便会一桩桩一件件地昭然于天下了。当历史在民间得以澄清,民间便获得主持正义的权力。而一向自以为能够玩弄民间于股掌之上的人,便不敢对民间颐指气使了。因为转眼也会被夹在历史中; 而民间将长存。理性的民间乃是这样的民间——除非它自己想要运动一下;披着任何华丽外衣的人,皆难以轻而易举地将它运动起来;它一定要运动一下的时候,并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具有充分理由的。即使理由充分,也仍理性。
是的,我以我眼看到,一个这样的民间,正在中国成熟着。理性的民间,才是有真力量的民间。伸张正义的民间,才是受尊重的民间。也只有这样的民间,才能被当成回事来对待,才能自己理直气壮地喊出“民乃国之根”,而不需要一味靠别人们的嘴来说。这样的民间,才配是“国之根”。
问:面对重重的社会问题,为何你的写作却越来越温和?
梁晓声: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自己最有兴趣的事; 从早到晚总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境况,另一种新的境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何别人更清楚这一点。
中国人所面临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危机一般空前严重。人想要的,总会以某种方式满足。画饼充饥的方式,于肚子是没什么意义的;于精神,却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许多种美的诞生是以另外许多种美的毁灭为代价的,我的牙齿习惯于咬碎一切坚硬的带壳的东西,而生活提供给我的新“食物”,既不坚硬也不带壳。它是软的、黏的,还粘牙,容易消化却难以吸收……虚伪——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本质上是欺骗自己;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本质上是对不起自己。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它的秘密。秘密是每一个人的第二性。
只有一样事物是不会古老的,那就是时间; 只有一样事物是有计算单位但无限的,那就是时间。“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一句话,细细想来,是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一千年以后金字塔和长城也许成为传说,珠峰会怎样很难预见。我愿做一扇敞开的窗,我愿做一面沉默的墙;更多的时候我宁愿是哑子,那么就不至于被迫开口,当众说话……
问:娱乐化时代还有必要坚持严肃的人文教育么?
梁晓声:娱乐本身也是分高低俗雅的。打麻将小赌小博是一种娱乐,打台球也是一种娱乐。好比满汉全席可以是一种讲究,青菜豆腐别有风味也可以是一种讲究。公开的下流也是一种快感。目前一部分人都巴不得有公开下流的权力和获得公开下流的快感呢!
当代人变得过分复杂的一个佐证,便是通俗歌曲的歌词越来越简明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和“女孩”。男人捏着话筒,长吟短叹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词句。“夜总会”和“卡拉OK”里的温馨情调本质上是虚假的。“精神”似乎早已被“气质”这个词取代了。而“气质”又早已和名牌商品的广告联姻了……就当前而言,同居和未婚而孕是青年“时尚”之一种;婚外恋和离婚是中年人的“时尚”之一种;被“啃老”已是老年人的“时尚”。人们宁肯彻底遗忘掉自己的天性,而不肯稍忘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是怎样的人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
没有幽默感的民族是缺乏亲和力的民族。但是丧失了庄重气质的民族也将是不可爱的。民族是需要文化培养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的话,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是堪忧的。我的眼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不少后代,自以为成熟了文化了的他们,人性中都或多或少有着非洲狮的恶劣狮性。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好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问:现在主流媒体对某事件的报道甚至都要引述网络上公众的态度,你怎么看待微博、微信等这种“短、平、快”的“意见表达”?
梁晓声:几年前,我曾应某网站之邀,在该网站开设博客,但终究难以为继。我不上网,也没有微博——但对网上言论的不负责任,早已有之。事实上我与电脑的关系一点儿也不亲密,我的手至今未在电脑上敲出过一个字。博客起初由网站打理。但凡是署我名字的所谓“博文”,确乎每一个字都先由我写在稿纸上。后来我便为此将文移送打字社,可渐觉麻烦。
一方面,我对网络亦敬亦厌,视之为公园中辟垃圾场、垃圾场旁设“民众法庭”的领地。奇树异花、正义审判往往与“私刑”现象“交相辉映”,穿插着骗子行径,假货叫卖声不绝于耳。然而网络终究改变了中国,故我的敬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意见表达的途径日益透明且多元化,我深心慰。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问:你平时不太用手机,几乎不上网,这会不会影响您与这个时代的沟通?
梁晓声:恰恰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
问:曾经有人找你去拍广告,为什么会请一位写小说的人去做广告呢?你后来为什么拒绝了?
梁晓声: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商业的时代。商业时代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是这样的:有人想挣大笔大笔的钱并不容易,而大多数人要想挣足够花的钱,又不那么难。
“微软帝国”的发展理念,说到底只不过是八个字——胜者统吃,无限占有;印刷机每天都不停地转动,成吨的纸被印上无聊的无病呻吟的玩世不恭的低级庸俗的黄色下流的文字售于人间。
在人欲横流的社会,善良和性行为同样都应有所节制。在商业时代,嘴是可以暗地里计价出租的。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为了盈利之目的,以对他人不利的广告词作招徕的方式,文明点儿说是不道德的。用老百姓的话,可斥之曰“缺德”!一种连抒情诗人也被逼得变成了斗士的时代,肯定是一种坏到了极点的时代。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城,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郁闷的中国人》《中国生存启示录》《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仍坚持纸笔写作,创作1600余万字。

